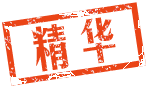抽完最后一只烟,李大叔嘀咕着,靠在院子里老藤椅上眯起了眼睛。 还是老东西好啊,瞧这把椅子,40多年了,孩子他姨夫亲自做的,椅身都睡得通红的了,篾条儿也掉了几根,可躺上就是踏实,那椅子被大叔睡熟了,服帖了,他一躺上去脑子就沉沉地回到了往事里…… 那白墙青瓦的,可是惹人眼,几乎是小时候淘气的军事要道了,为了摘石榴,掏鸟窝,在白墙青瓦上爬来爬去,因为这个没少挨娘的打,那一个缺口的青片瓦,还是为了讨二丫喜欢,要摘最大的石榴,硬是给蹬碎了。如今的二丫呢,早成了二狗子的老婆子了。 香啊,可是真香啊。老爹、三叔、二舅,一帮子都是靠那酒缸子掏钱,养活几大家子,头道好酒,他们就封好,沿着墙摆一溜,逢年过节的启一坛子,那叫个香,香透几条巷子!那叫醉,当晚醉倒一院子人,第二天,醉倒村里的大黄狗。 那道门,背着媳妇跨过,脊背一颤一颤的,我知道,盖头下的她笑得欢实。她大红的袄子总是在我眼前晃啊晃的,美瞎了我的眼睛。那一天,银杏树叶铺满了院子,象一层金黄的地毯。转眼间,一个两个的小崽子们就在地上撒欢儿了,孩她娘拿着扫帚追。 走了,爹和娘盖着白布从这儿走了,唢呐声呜啦呜啦地吹得那个难听。走了,孩她娘也走了,红盖头进来,白布出去了。那一天,石榴花儿开得分外红,就像她过门时的脸 。那年之后,石榴就没有结果了。从墙角攀出的绿萝,爬满了墙,缠缠绕绕的,他知道的,这是孩他娘留给他的,是孩她娘不放心他,知道大叔喜欢躺在椅子上打盹,留点儿阴凉护着他。 小崽子们长大了,看不起这儿了,嫌弃这里潮湿土气了,一个个吵着等拆迁,昨晚吵一宿,想住洋房。呸!说这里老了,败了,生活不方便了,门一摔就走了,把门栓儿都震掉了。
咳咳,剧烈的咳嗽声,迷迷糊糊,李大叔仿佛听到孩子娘的声音:老头子,随孩子们吧,你也老了,听话吧,入秋了,别在院子里睡着了…… 听话,听话,我就是不听,走吧,都走吧……就不听话……这是我们的窝。
|